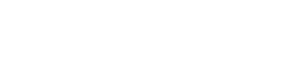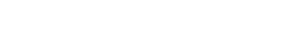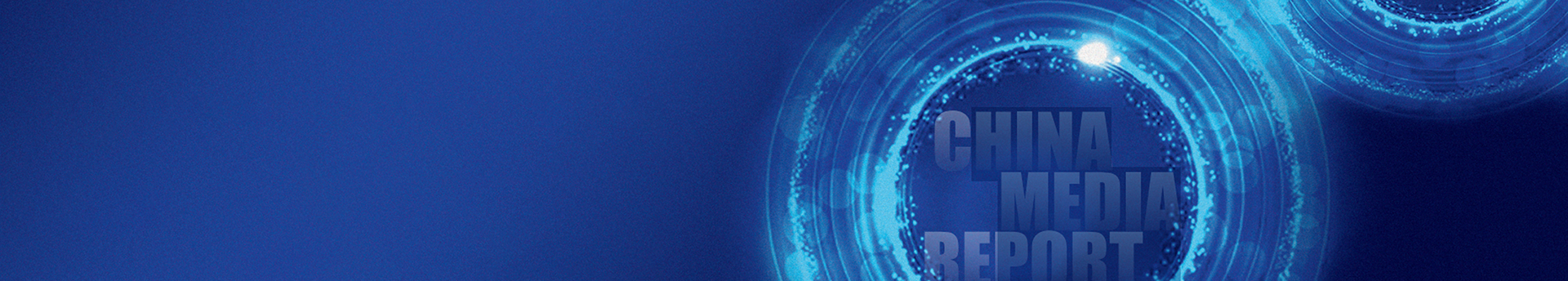数字传播时代崛起与大众传播时代的终结——数字时代以人为本的传播范式与新的学科想象力
摘要
今天,传播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枢纽,传播学也第一次置身于时代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智能传播时代的全面到来,标志着社会信息传播越来越走向技术主导,反而迎来了回归以人为中心的新契机。以人为本的传播学能否成为传播学新范式的首要标志?我们深入数字传播范式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对信息传播的构成、传播的主体、内容、速度、受众和效果等要素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科学理论、基础原理、基本技术、核心应用以及传播机制等层层推进的传播发展与变革进程进行了深度剖析。数字传播每一次新机制的诞生都是以传播信息量、速度和效率的数量级的提升完成跨越式的发展,技术驱动的生产力的内爆,完成了数字传播超越大众传播实现所有人成为传播真正主体的必由之路。通过大众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微观分析,呼应了百年传播进程的初心和使命的回归,面向新的数字文明的到来,传播学可以展开想象力的翅膀,重树使命和学科尊严。 关键词 数字传播;大众传播;范式转变;结构性;传播要素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9)和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07)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方兴东,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互联网历史与文化、新媒体。 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新媒体、文化研究。 一、以人为本的传播学, 赋予了学科全新的想象力 今天,随着智能传播逐渐成为主流,数字传播时代全面到来,传播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而新闻传播学的内卷化和路径依赖的困境也日益显现,甚至已经进入旧有路径的锁定效应。其直接表现为对外部环境的巨变失去了应有的敏锐度和反应能力,无法积极拥抱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最新挑战。相较于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时代,衰落已成现实。对应于数字时代的数字传播虽然已经快速崛起,[1] 却依然有待学术共同体的全面认同和新知识体系的重构。传播学的未来无疑需要立足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融入鲜活而生动的社会实践,超越技术维度,聚焦未来人类的生存状况。 昆德拉认为,失去想象力的小说,实质上就死了。“我只知道自己相信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假如它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之所以在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如《圣经》一般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因其触及了一个学科的灵魂,即“社会学应该如何想象”的核心问题。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必然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结构是历史事件的产物。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所谓“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不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2] 然而,当前传播学处境和彼时的社会学何其相似。 今天的传播学,必须挺进互联网浪潮的主战场,必须置身近80亿人口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的风头浪尖,为所有民众、企业、政府等提供在新时代更好生存、发展与治理的新的知识体系,回应技术浪潮下人类社会未来究竟向何处去的根本追问。2020年5月31日,全球人口接近78亿,网民数量已经超过46亿。[3] 华为在2016年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表示,预测到2025年,个人智能终端数将达400亿,物理联接将达到1000亿,增长幅度超过10倍,而虚拟联接将达到万亿,增长幅度将达100倍。智能终端数、物理连接与虚拟联接在数量上的爆发性增长将引发质变,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全联接的世界。那时候,全球人口都将或多或少、主动或者被动地联在网上,真正意义上的“离线”将从此成为历史。 随时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的发展,人类信息传播已经从自上而下、一对多、单向度、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全面走向自下而上、多对多、实时互动、开放式的大集市模式。[1] 传播从由少数人、少数机构主导和控制的行为,变成了当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传播者和主导者的新局面。恰恰因为技术在传播中的作用和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更需要将“人”真正回归到传播的中心。只有以人为本的传播学成为新范式的首要特征,才能确保人类在数字传播的波涛汹涌中走向安身立命的新文明。 图1 传播学的范式转变进程 今天,传播学从学科的反常阶段和危机阶段开始进入范式革命阶段,“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当然,传统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依然根深蒂固。面对新的时代变革,学术共同体旧有的认同在坍塌,新认同在崛起过程中,开始进入真正结构性变革的新阶段。传播学从经验主义主导的内容和效果研究,到今天堪称硕果累累的媒介分析,显然,依然难以走出旧有路径的“锁定”效应。那么,以人为本的传播学是如何发生的?又将走向何方? “我们正处于技术革命之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新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置身于疫情漩涡中的资本市场的弄潮儿、桥水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倒显得格外冷静理性。[4]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程的分水岭,标志着人类传播范式从大教堂模式的大众传播全面正式转向了大集市模式的数字传播。[5] 特别是,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以及脑机接口、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突破,一向处于传播学研究近乎中心地位的媒介也面临挑战。从代表媒体机构的媒介,到作为载体的媒介,到作为表现形式的媒介,直到正在到来的微观粒子的媒介。媒介不再是信息的论调已经大势所趋。媒介虽然没有消亡,但是,的确在无可挽回地边缘化。被不断缩微和流失的媒介,其价值与作用也日渐式微。而“媒介不再是信息”,反而可能让传播学的走向更加开阔。 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在1950年的著作中提出,它甚至有可能将一个人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6] 汉斯·莫拉维克认为人类与其说是身体的存在,不如说在本质上是指信息模式。如果一种科技能够复制这种模式,那么它就掌握了一个人的至关紧要的方面。为此,莫拉维克还设想了将人的意识下载到电脑中,并且可以输入到新的模型之中,躯体就成为一具空的外壳。[6] 当然,上述设想到今天依然还是想象。但是,信息传播的去“媒介”化趋势是非常清晰的。无论是作为机构的媒介,还是作为载体的媒介,抑或作为内容表现形式的媒介,乃至今天电磁波、光子和量子等微观粒子的媒介,都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的消解、缩微和去意义化。今天数字传播显著地推进了这个进程。 任何物质,任何媒介,都是信息的束缚。技术的发展就是挣脱束缚,帮助信息从媒介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使得信息更加自由。正如凯瑟琳·海勒斯所言:“黑客们并不是唯一相信信息渴望自由的人。信息的伟大梦想和承诺是它能够摆脱统治着这个不可永生的世界的物质束缚。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所建构的信息,那么,我们也能够像永生的神一样自由翱翔。”[6] 虽然,这样的现实目前依然是梦想,只要信息/物质的双重性依然存在,媒介就永远存在。尽管未来的媒介可能进一步微小到量子以及,研究媒介要具有粒子物理学家的基本功底。 尽管一个学科的范式转变,有可能通过大师的出现而快速完成。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在某种内在核心因素驱动下,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自然演进过程。然而,学科的范式转变,与产权明确、所有权和管理权清晰的企业不同,是学术共同体的创新与变革过程,现实学术共同体的范式转变更为错综复杂。但是,从局部的创新,升级的冲突与博弈,到普遍性的共识,进而完成全局性的转变。也有着基本的内在周期、逻辑和规律。当传播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和中枢,当传播越来越成为个人、企业、机构、政府等社会行为体生存的基本条件,传播学新的研究领域豁然开朗。除了传播的技术属性,传播的社会属性也可以海阔天空。当然,与各个学科的融合、博弈与碰撞也将更加剧烈。 二、传播学学科与人的距离 西方史学家认为西方人一直在“理性”的阴影下思考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又深植于西方人对传播问题的认识之中,通过将传播中的各个要素从传播实践的过程、环境以及要素的相互关联中剥离出来。在加深对传播要素的认知的同时又遮蔽着传播所固有的情境性、历史性、整体性和主体间性。”[7] 关于传播学的知识史,Everett M.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已经做出了充分的梳理。[8] David Paul Nord(2007)和John Durham Peters(1999)对传播学之特定思想,技术,行业和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然而,一种试图将传播观念与媒体技术发展相分离的实践却面临极大的困难。在传播学领域,许多学者试图探寻一种关于人类交流的通用解释理论。他们认为这种“通用理论”必须能够预测未来并解释过去,也就是,必须有涵盖各种传播的一般理论。它必须适用于人际交流,大众传播,人机交互,人类媒体互动,社交媒体,数字游戏,虚拟现实等尚未发明的所有人类交流类型。早在1970年代,Kenneth R. Williams致力于扩大传播研究中“科学”一词的有效性范围,继而提供一种人文主义范式,以补充传播科学传统物理主义范式的主题,方法论立场和认识论目标。他认为,一门人类传播科学应该将交往实践的形成经验作为主题,它的主要目标不是最终的传播知识,而是对人类状况的最终关注。[9] 在《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与“人”学迷失》一文中,学者试图探寻“科学”对传播研究的异化,以及“人”的回归。[10]如今,传播领域已经从以“机器为中心”的传播转变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对用户的透明度越来越高。计算和通信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逐渐成为全球技术挑战和重点研究方向。Annie Lang将传播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包括人,消息,媒介和位置。他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对传播研究进行了概念化,试图提出一种“动态的以人为中心(Human-centered)”的传播系统理论,并且,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重新概念化了所有主要的传播类型。[11] 在对传播学思想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夏冰等学者在《从“人”出发的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研究维度的再思考》一文中对各方理论中关于人在传播中的存在方式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试图以从“人”出发视角,从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当代传播学。尽管作者对思想史的考察相对完善,但是,对技术层面的思考却略显不足,换言之,对传播学自身的物理范式转变与人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也十分必要。 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传统下的现代性批判始终围绕着“大众传播”领域展开。尽管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文化研究,从哈贝马斯到麦克卢汉,对于大众传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所“突破”,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数字社交网络的扩展以及全球范围内社交运动的迅速兴起,媒体和传播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12] 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集体行动都象征着“来自下方的压力”。新形式的社会集体行动扩大了公民,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媒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和关系范围。[13] 新的传播范式所采取之“旧”思维仍然顽固,同时,这要求传播学者应注意重要的变化和动态。Robert Craig(2018)将传播学看作是一门实践学科,并对其作出概念性解释,即传播学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学科,其基本目的是通过促进关于传播实践的规范和技术方面的元论述来培养社会实践的社会文化构成领域。传播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并且以实践为导向。也正如Robert Crai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将自己的领域重新考虑为‘实践学科’。否则,我们将忽视在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反思行动。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常识,并且如果我们继续与自己交谈,却忘记了象牙塔之外的社会,机构和媒体行业参与者,那么对于媒体和传播研究而言,无论其关键或行政性质如何,它都是死胡同。”[14] 从(大众传播的)“旧思维”到“新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微观(使用者)层面的关照。从计算机、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更多的兴起于设计学(关乎所有人造物的科学),即“以人为中心设计”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喻国明等人通过对传播媒介的分析认为,传统以媒介物理属性为分析逻辑的研究范式不再适应当前更加复杂的媒介环境和媒介现象以及用户的使用行为,并提出以人为本的媒介观。[15] 除此之外,通过对中国互联网25年发展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有学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是一个“充满创新、不断走向以人为本的过程”。[16] 三、数字传播的微观分析: 结构性的要素与关系 随着疫情时期“健康码”的流行和常态化,随着抖音、快手等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应用爆发,新的技术主导、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快速崛起。原来Facebook、微信、推特等以人际自传播为基础的社交媒体遭遇全新挑战。互联网超级平台不但主导了社会信息传播,而且对社会经济、活动乃至政治运行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拜登政府组建了主张加强反垄断的超级阵容,开始启动全面反垄断浪潮。中国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国家年度工作重点,[17] 欧洲推出《数字市场法》草案,通过新的“守门人”制度,期望通过新的制度范式超越传统事后监管的反垄断法。驯服超级网络平台,成为欧美和中国等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这种背景下,呼唤以人为本的传播学新范式,有着特别的时代意义。 在当代,两个主要动机驱使学者们尝试建立新的知识学科。首先是以新的方式研究旧的学科问题,或者该领域本身是新的。其次是新学科通常需要大量的学术资源和可观的预算。[18]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传播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当代传播学中使用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论常常看起来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相互交叉。关于学科状态的任何描述都受到范围的限制并且带有偏见。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该领域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普通学者处理和消化新信息并保持概览的能力。[19]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绪论中写道:“如果我们主要是寻求和考察那些从科学教科书中得出的、不含历史的旧规老套的问题的回答而继续使用历史资料的话,那么,新科学观就将不可能从历史中产生。例如,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内容是唯一地由书中各页所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这样一种科学观大大影响了我们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理解。” 库恩说的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的路径依赖问题(Path Dependence)。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所以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传播学领域的每一位专家学者都是传统范式学习出来的,塑造了基本的知识体系,必然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且在未来职业生涯中不断自我强化。因此进入锁定状态,想要挣脱就会十分困难。要颠覆旧有范式,塑造新范式,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研究传播学范式转变的学者,都希望从传播学近百年的历史中去找到答案。这无疑是缘木求鱼。库恩认为:“科学并不是通过一个个发现和发明的积累而发展,而是一个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渐变和激变相结合的过程。” 库恩提出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即相继范式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不可调和的。传播学的新范式,也必须首先跳出大众传播理论的固有框架。才可能豁然开朗。 范式转变,其实就相当于经济学所说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结构性的变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要深刻理解新旧范式,进行结构性分析非常有必要。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微观的结构性层面,对相关要素与关系进行分析和探究。结构性分析就是对事物所在领域的结构进行分析, 或者说是对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及其对比关系变动规律的分析。以揭示目前事物所涉及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图2 传播学范式原有研究框架与新范式下以人为本的研究框架 图3 传播学新旧范式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均衡示意图 首先,我们将从社会信息传播的占比的变化,尤其是数字传播机制在其中占比压倒性的优势,作为数字传播范式的实证。然后,我们深入考察数字传播的过程、速度、传播主体、内容、受众和效果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透视数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根本性变化。以此思考“人”在传播中的新处境与新位置。 (一) 数字传播的要素之一: 传播信息量看范式之变 自通信出现以来,信息已经通过非电子(例如光学,声学,机械)手段发送。自电话问世以来,模拟信号数据已通过电子方式发送。但是,现代的第一个数据电磁传输应用是电报(1809)和电传打字机(1906),它们都是数字信号。哈里·奈奎斯特(Harry Nyquist),拉尔夫·哈特利(Ralph Hartley),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人在20世纪初期就进行了数据传输和信息理论的基础理论工作。在过去20年中,全球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也改变了世界的社会愿景。数字时代是由包含信息、知识、思想和创新的连续数据流决定的。数字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塑我们的社会、经济和产业。移动和云技术、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医疗服务、交通、能源、农业、制造、零售和公共行政等许多领域提供了难以想象的机会,推动了增长,改善了公民的生活和效率。他们还可以通过帮助决策者做出更好的决定和吸引公民来改善治理过程。特别是,互联网在促进民主、文化多样性以及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等人权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调查得出的一个最大趋势是“数字和通信革命”。数字革命创造了新的角色(如搜索引擎优化经理和社交媒体账户经理)、新类型的组织(云计算提供商和社交媒体机构),甚至经济的新部门(数字安全和数据科学)。数字化的影响也成为更广泛的经济中就业增长的催化剂。 我们每天产生的信息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1950年代开始,公共数字数据传输首先利用现有的电话线进行拨号,直到2000年代实现宽带。无线革命作为无线网络的引入和普及,始于1990年代,并通过广泛采用基于MOSFET的RF功率放大器(功率MOSFET和LDMOS)和RF电路(RF CMOS)实现。无线网络加上2000年代通信卫星的激增,使得公共数字传输无需电缆。这项技术直接影响了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数字电视,GPS,卫星广播,无线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国家数据传输系统的组织始于1972年,该系统最终将向所有部委提供数据传输服务。该系统的第一阶段是建立电报式网络,以高达200位/秒的速率传输信息。当前,数据传输是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1955年,全世界不超过1000个数据传输终端单元。到196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5,000,到1970年,上升到150,000。到1975年,这个数字有望超过100万。在许多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为70-100%。 图4 数字传播基础设施的演进历程 在技术层面,通过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化(括号内数字成为主导阶段)过程可以看出数字化更迭。从模拟计算机到20世纪50年代数字计算机成为主导、电传到传真(1980年代)、留声机圆筒、留声机唱片和盒式磁带到光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VHS到DVD(2000秒)、模拟摄影(照相底片和照相底片)到数字摄影(2000年代)、模拟电影摄影(电影库存)到数字电影摄影(2010年)、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预计20世纪20年代)、模拟无线电到数字无线电(预计在20世纪20年代)、胶印到数码印刷(预计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从1980年代的1G模拟通信时代向2G数字通信时代、具有高速分组业务的3G移动通信制式、全IP数据网络的4G时代,到5G的万物互联时代全球性数字传播格局的奠定,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见图4),能够清晰体现出每一个转变过程的不同特点。[5] 按照我们目前的速度,每天有250万字节的数据被创建,仅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就生成了全球90%的数据(Marr,2018)。截至2019年底,全球手机用户为47.8亿(占世界人口的62%)全球互联网用户约为46亿(占全世界人口的59%),2017年6月为38亿。互联网全球渗透率从2005年的近17%上升到2019年的53%以上。[3] IDC在其对2017年及以后的IT行业预测中宣布,数字化转型将在未来三到四年内实现宏观经济规模。到2018年,物联网设备的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带动200,000个新应用程序的开发。到2020年,云服务支出将超过5,000亿美元,是当前水平的三倍。2019年,全球对数字化转型计划的投资将达到2.2万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近60%。Gartner预计,到2021年,财务和医疗保健领域数字化程度将达到更高的水平,所有社会活动中将有20%涉及到前七大数字巨头。[20] 在社交媒体的使用方面,2019年比2017年增长了33%。截止2019年底,全球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达到37亿。在电子商务方面,网上购物的人数从2017年的16亿活跃用户增加到2019年的近20亿。这已经是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据纳斯达克(Nasdaq)报告称,他们预计,到2040年,大约95%的交易将在网上完成。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的Facebook拥有20亿活跃用户,即世界70亿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活跃在Facebook上。根据Facebook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天有15亿人活跃在Facebook上;欧洲在Facebook上的用户超过3.07亿;每天上传的照片超过3亿张;每分钟上传评论51万条,更新状态29.3万条。此外,作为数据存储库“爆炸”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物联网所连接着的“智能”设备(从2006年的20亿台设备到2020年预计的2000亿台设备)在收集各种数据的同时与人们进行互动。 尽管社交媒体的势头强劲,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电子邮件的使用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据Radicati集团的《2019-2023年电子邮件统计报告》指出,2019年每天发送2,930亿封电子邮件,预计到2023年,这一数字将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长到3,470亿封。根据同一份报告,2019年有39亿电子邮件用户,到2023年底将增加到44亿。 图 5 全球存储、通信和计算信息的技术能力(Hilbert,2011)[22] 图6 数字宇宙的估计大小(Estimated Size of the Digital Universe)[21] 新的IDC数字宇宙研究(Digital Universe study)预测,2020年,数字宇宙将达到40 ZB,即40万亿GB数据,或地球上每个人拥有5,200 GB数据,比2010年初以来增长了近50倍。与物理宇宙类似,数字宇宙(Digital Universe)的体量也很惊人。到2020年,数字宇宙所包含的数字位几乎与宇宙中的恒星一样多。它的规模每两年翻一番,到2020年,数字宇宙(我们每年创建和复制的数据)将达到44兆字节或44万亿千兆字节。 图7 1986-2014年模拟与数字转换 南加州大学的马丁·希尔伯特(Martin Hibert)系统研究了“全球信息存储、传输和计算的能力”,数字卫星电视进入了数字时代,在2007年接收了全部数字广播信号的50%。2007年,所有广播信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数字格式的。1986年以来的信息传播以固定电话为主,而邮政信件仅占0.34%。1993年以固定电话网络的数字化为特征。1990年作为从模拟到数字的转折点,以及2000年爆发的互联网革命,在短短7年中,宽带互联网的引入有效地使世界电信容量增加了29倍。2007年,移动电话网络越来越受到数据流量的支配(移动数据为1.1%,移动语音为0.8%)。[22] 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1986年人类全球双向通信的信息量中,固话通信量的比例占到80%,独领风骚。1993年,人类所有双向通信的信息量中大约只有1%是通过互联网传送的;到2000年,互联网通信量就开始占比过半,达到51%。而到2007年,人类所有通信信息超过97%是通过互联网。另外3%的大致构成是,固话语音通讯占1.5%,移动电话语音通讯占1.1%,移动数字通信占0.8%。如图7所示,从1980年代末期的全球以数字格式保存的信息还不到1%、 到2000年75%的信息以模拟格式存储、到2007年数字格式的信息占比高达94%,再到2014年,数字格式的信息占比已经超过99%,模拟的已经不到1%。[22] 可以说,整个世界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传播毫无疑问已经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绝对主导。 (二) 数字传播的要素之: 传播主体与受众之变 大众传播的内容生产者也就是新闻工作者。根据统计,美国包括记者编辑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内的新闻从业人员为2008年为11.4万人,2019年下降到8.8万人。他们构成了美国报业的核心内容生产。 网络传播的门户时代,无论是美国的雅虎、美国在线还是中国的三大门户,虽然内容大多数为专业性内容,依然是由编辑把关,集中控制,与大众媒体一样还属于一对多、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但是,与传统媒体相比,内容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网站一般不自己生产内容,而是通过汇聚和集成各方面的内容,包括传统大众媒体的内容。当然,因为网络独特的积累性和无限性,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开始成为内容的创造者。网络媒体事实上是编辑主导内容,可选择的内容比起传统媒体有了数量级的扩张。包括传统媒体历史内容,在网络媒体得以更全面呈现。因为网络,内容第一次得以不断积累。 内容生产的爆炸性成长源自于Web 2.0的到来。博客成为第一波浪潮。博客迅速在全球爆发,在推特(Twitter)成立的2010年,全球网民数量为19.7亿(截止2010年6月),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Royal Pingdom统计,全球博客数量为1.52亿个,2010年Twitter新增账户1亿个,发送的信息为250亿条,截至2010年底,Facebook用户数量为6亿,Facebook上每月共享的信息量为300亿条。YouTube网站每天视频浏览量20亿次。平均每分钟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的视频时长为35小时。截至2010年9月,Flickr网站托管的图片数量为50亿张,每月上传到Flickr网站上的图片数量为1.3亿张。 而到了今天,全球网民超过45亿。根据Statista的数据,2019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达到27.7亿,比2017年的24.6亿增加了3.1亿。预计2020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将达到38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将近80%。 2019年5月每天发推数量大约是5亿条。月活跃用户3.33亿,其中美国之外用户为2.62亿,占比达到79%。美国月活跃用户大约是4835万。日本用户3565万,俄罗斯1390万,英国1370万。2020年第一季度,推特可货币化日活跃用户(mDAU)为1.66亿,而去年同期为1.34亿,同比增加24%,为迄今为止最高的同比增长率,主要受疫情影响。2019月2月,Twitter对业务衡量指标进行了调整,将不再披露MAU(月活跃用户),而是启用新的指标——mDAU(可货币化的日活跃用户)。当时,推特的月活跃用户大约是3.33亿,比一年前的3.36亿有所下滑。其中80%用户通过手机使用,视频内容更是93%来自手机。42%的用户每天至少会上平台一次。 截止2020年4月底,Facebook日活跃用户(DAU)为17.3亿,同比增长11%,月活跃用户(MAU)为26亿,同比增长10%。“全家桶”(包含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日活跃用户人数为23.6 亿,月活跃用户人数为29.9亿。而全球网民数量大约为45亿。“有史以来第一次,每月有超过 30亿用户使用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或Messenger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上说道,”仅 Facebook MAU就有26亿,每天有23亿用户至少使用我们的一项服务。”扎克伯格表示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通过WhatsApp和Messenger发送的短信数量增长了50%,语音和视频通话数量增长了一倍还多。在意大利宣布锁城之后,用户在Facebook 所有应用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了70%,Instagram和Facebook Live浏览量一周内翻倍。 2020年6月,微信的用户数量已经高达12亿人,其中月活跃使用人数也达到了10亿人之多。而与此同时,短视频进入全球爆发阶段。Sensor Tower商店情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4月,字节跳动旗下抖音及海外版TikTok在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总下载量已经突破20亿次,距该应用创下15亿次下载量仅5个月。2020年第一季度,抖音及海外版TikTok在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共获得3.15亿次下载,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根据CNNIC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超过9亿大关,其中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50亿,较2018年底增长1.26亿,占网民整体的94.1%。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较2018年底增长1.25亿,占网民整体的85.6%。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络视频应用的用户规模、使用时长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智能传播的主体不再是用户,而是智能硬件和算法。根据IoT Analytics数据,2020年全球活跃的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100亿台。到2020年底,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将利用物联网和传感器数据,并结合分析驱动的认知能力,将效率提高10%。根据IDC白皮书,世界数据的总和将从2019年的33个zettabytes增长到2025年的175ZB,复合年增长率为61%。预计在2025年,物联网设备将产生超过90 zettabytes的数据。到2025年,49%的数据将存储在公共云环境中。到2025年,将近30%的数据将实时消耗。到2025年,普通人每天将有近5,000次数字互动,高于2019年人们平均700到800左右。“如果有人能够将175ZB存储到BluRay光盘上,那么你就会有可以让你登上月球23次的光盘”,Reinsel在视频中说。“即使你可以在今天最大的硬盘上下载175ZB,也需要125亿个硬盘。” 数字传播的内容既包括传统媒体的专业内容,也包括用户创造的内容,还包括智能终端收集、生产和处理的数据。内容的内涵已经大大拓展。同时,拓展的还有受众。从社交媒体开始,数字传播就进入一个“产消”合一的进程。今天,全球60%的民众已经上网,他们既是传播内容的主体,也就是传播“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数字传播的受众和消费者。而万物智联时代,除了人之外,更多的机器设备和物体成为了数字传播的“受众”之列。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人的处境究竟是进一步加强还是进一步边缘化,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焦点。 (三) 数字传播的要素之: 传播速度之变 过程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播过程,指的是具备传播活动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的过程。无论是内容的生产过程,还是内容的传播过程,甚至包括媒体的制作过程。大众传播的很多奥妙都在过程之中。包括内容的把关、审核、反馈以及内容的控制和审查,一切艺术都在过程之中体现。没有过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数字传播的进程中,过程逐渐趋于消失,无论传播内容的生产还是送达,都趋于即时。传播过程与速度之变,呈现了数字传播与大众传播完全不同的景观。 麦克卢汉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媒介即信息”,亦即传播信息的内容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什么媒介形式去承担传播任务,媒介形式的差异比内容本身的差异更重要。当代人们所处的媒介系统几乎已然全部由准光速的媒介(互联网、实时电视、移动互联网等等)所构建,是什么媒介来传送内容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速度差异使得媒介的本质截然不同。美国学者H.弗雷德里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推算:如果以公元元年人类掌握的信息量为单位1,那么信息量的第一次倍增,花费了1500年;第二次倍增,花费了250年;第三次倍增,花费了150年;进入20世纪后的第四次信息量倍增,所需时间进一步缩短为50年。其后,倍增速度骤然加快,在1950年代,10年内就实现了倍增;接着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间周期进一步缩短为7年和5年。根据推算,目前人类社会信息量倍增的时间仅仅需要18个月至5年。 199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信息传播发生巨大变化。从那时起,这种通讯媒介的急剧变化已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媒体的认知,时间和空间的使用以及媒体的可达性和控制。在当今的数字通信时代,时间已经通过减少空间中不同点之间的距离而被压缩,并且空间感使人们感到本地,国家和全球空间已经过时了。[23] 此外,数字媒体的可达性现在可以扩展到所有人,而不是有限的受众。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对信息产生和传播的控制不再是“特权”,而是由所有个人平均共享。在基础设施方面,数据传输用于计算机网络设备中,例如调制解调器(1940),局域网(LAN)适配器(1964),转发器,转发器集线器,微波链路,无线网络访问点(1997)等。1980年代初期,调制解调器的传输速率为200波特(约200位/秒),然后为800波特,很快达到2,000波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电话网络中,数字通信被用于通过脉冲编码调制(PCM),即采样和数字化,结合时分复用(TDM)(1962),在同一条铜缆或光缆上传送许多电话呼叫。电话交换机已变成数字化和软件控制的形式,从而促进了许多增值服务。例如,1976年推出了第一个AX电话交换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使用综合服务数字网络(ISDN)服务就可以与最终用户进行数字通信。自1990年代末以来,诸如ADSL,电缆调制解调器,光纤到建筑物(FTTB)和光纤到户(FTTH)的宽带接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小型办公室和家庭。IP电话和IPTV之类的分组模式通信代替传统的电信服务。在巨大的传输计算机数据的需求以及数字通信的能力之下,数字通信迅速淘汰模拟通信。 图8 推特出现前与后信息创建和传播的情况对比 信息传播速度是衡量媒体传播方式是否迅速的一个标准。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即时性相对较弱。因为传统媒体如报纸等出版需要经过编审、校对等一系列过程,跟不上信息变换的速度。即时性较强的则是新媒体传播形式,如微博、抖音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微博,微博是一个可以让各个地方的人们都聚在一起讨论某个事件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信息的传递则真正做到了即时高效。根据博雅公共关系公司(Burson-Marsteller)针对推特出现前后的信息创建和传播情况的调查,通过从信息创建、信息发布和观众呈现三个方面表现一个事件爆发后信息传播速度情况。从图8可以看出在推特出现之前,一个事件的发生从目睹到报道者到达需要花费1个小时左右;新闻报道者将新闻带回新闻机构再到新闻台需要花费2-2.5小时。经由新闻台,线上发布在事件发生2小时后开始发布信息,也就意味着观众最快能在事件发生2小时后获取事件相关新闻;广播发布则需要近2小时40分,观众获取信息基本与发布时间相一致;到电视发布事件信息需要花费3个小时,观众获取事件信息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报纸和杂志则需要花费8个小时编辑和发布。自推特之后(图8),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事件发生时,以往的观众成为亲历者、报道者、编辑者和发布者,直接记录和发布事件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事件传播过程的消失。 除此之外,光缆传输承担了近95-99%的国际传输数据。微软、Facebook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Telxius在大西洋上已铺设的光缆Marea,每秒可传输160TB的数据,速度比普通家庭网络连接快1600万倍。亚马逊不久前也宣布打造自主的AWS海底光缆,用以降低时延。 “技术是速度的表象,速度才是技术的本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见证了蜂窝通信技术从2G全球移动系统(GSM)到4G长期演进高级(LTE-A)系统的快速发展。主要的动机是需要更多的带宽和更低的延迟。数据传输速率已从2G的64kbps提高到3G的2mbps和4G的50-100mbps。5G将提供与密集异构网络的无缝兼容性,以满足实时流量的高需求,从而最终用户将体验到与网络的平滑连接。[24] 到了新的智能传播阶段,信息传播的速度进一步突破了人正常的生理反应速度,人在传播中的主动性角色会不会从此丧失? (四) 数字传播的要素之:传播效果之变 传播“仪式观”的提出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尖锐地指出:“严格说来,并没有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是一种近来的文学类型……一种自我意识的创造(现在成了一种无尽的再创造),筛选、分类、再整理累积的文本残骸构成一种统一的叙事。这种叙事最终服务于一系列目的:主要是关注、证明、合法化大众媒介这20世纪的‘发明’,引导相关的专业教育与研究方向、赋予其学术地位。但是,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历史 ( innocent history) ,因为它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发明出来的:为了培植忠诚、解决争端、指导公共政策、扰乱对手以及合法化制度;简言之,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就是 20世纪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25] 詹姆斯·凯瑞所说的大众传播的困境是真实的,但是,在数字传播时代,传播的角色、作用、效果和价值已经几经突变,与大众传播相比已经今非昔比。 (五) 数字传播的要素之: 传播类型是如何打通与融合的 大众传播范式下,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是泾渭分明,各成体系。但是,在数字传播范式下,各大传播类型通过数字化,走向了相互联动、相互协同的融合之路。深入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有助于我们更加精细地洞察数字传播的内在机制和动力。 图9 大众传播范式与数字传播范式的转变进程 虽然数字传播历史悠久,但是数字传播触发传播学的范式转变,还是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开始、新媒体崛起。在产业界和资本界强力推波助澜下,学术界也直接感受到技术创新和应用突破带来的,对传统基于大众媒体的传播学的冲击。 技术是变革的基础,是底层的驱动力。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是宏观的表现。产业界的发展与壮大,是介于微观技术和宏观社会的中观层面。但是,变革的进程和阶段是彼此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参照技术进程,以年代为阶段,考察传播学的进程。 1990年代:范式转变的酝酿期,少数梦想家主导的进程。新理念,新概念,新思想开始萌芽,孕育。直接的原因就是互联网商业化浪潮,新的网络传播机制崛起。出现了明显有违于传统范式的各种反常行为与现象。 2000年代:范式转变的冲突期:进入21世纪,随着博客、播客等社交媒体逐渐萌芽,学术界一批敏锐的学者率先感知到新的变革力量,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主导的进程。一批先行者发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和判断,新的范式初现轮廓,但是,这个阶段旧范式处于巅峰阶段,依然具有强大的主导力量,新范式遭遇旧范式的全面挑战和不认同。 2010年代:范式转变的胶着期。随着Facebook、推特、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强势崛起,成为社会的主导传播范式,新范式已经展露无遗,学术界的主流的现实主义者也认清了方向。新范式势不可挡地崛起,而旧范式依然不甘心轻易退出舞台。这个阶段新旧范式处于胶着阶段。问题清晰了,共识有了,方向有了,但是,具体的进程和目标,新范式的基本架构等都还不够明朗。 2020年代:范式转变的革命期。随着智能传播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又一轮新技术新应用的推波助澜,传播的新范式已经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学术界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也加入进来。旧范式没有消失,但是开始退出舞台中央,和新范式还会长期共存期,但是,社会和学界的主流都普遍接受新范式。范式的革命就在这个阶段中自然而然中完成。 2030年代:范式转变的奠定期。随着智能传播也走向主流,大集市模式的新范式依然会有怀疑和反对者,但是,已经明显式微。新范式成为真正主导性的主流范式,成为新的常规科学。刚刚立足已稳的新范式,会不会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主导人类的“奇点临近”等下一波新技术变革中成为再次被颠覆的对象,这就需要等候时间去慢慢回答。 百余年大众媒体所树立的大众传播模式,在数字传播碾压式的优势下,承受巨大的发展与生存压力,但是,并没有因此土崩瓦解,而依然呈现顽强的生命力。作为新范式超越和战胜的对象,旧范式的大众传播,也在经历浴火重生,与时俱进。大众媒体通过内容在数字传播新机制的多渠道传播,以及自身积极介入数字传播,开启了大教堂模式的数字化之路。 四、重新再出发: 追问传播学的使命与价值观 传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成为最一般的社会现象和活动,成为社会形态和运行的基本方式。所以很多人认同,传播学应该成为一门基础学科,乃至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是,遗憾的是,现代传播学正式诞生70多年来,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显学。学科的早期奠基人和开拓者,很多陆续都离开了传播学,充分说明了传播学自身凝聚力的不足。甚至到今天,传播学还没有超越新闻学的基本路径。传播学的现实尴尬可想而知。 罗杰斯在整理施拉姆最后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传播学的开端》时候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学科的一个重要统一体之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它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期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势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8] 施拉姆设想中的传播学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科学的基层,甚至共同的基石。这一梦想迄今依然显得遥不可及,但是,又显得如此触手可及。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之后,信息传播的确成为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基层。那么,传播学的未来究竟该如何? 一门学科的范式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理念(范式的精神内核,即世界观和价值观)、话语(核心概念、理论、制度或规则,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技术(方法、范例、模型或模式,是支撑范式的骨架)。[26] 其中,价值观是最根本的。一门学科之所以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首先在于共同的价值观。没有价值观基础,共同体就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和凝聚力。显然,传播学的困境首先在于自身使命和价值观的不明确。传播学究竟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想和目标?传播学自身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观和愿景?迄今,传播学的著作几乎没有对此做出统一的回答。 公共成为新闻业的“上帝用语”和终极术语,扮演着公众的代言人。新闻媒体担负的社会舆论监督权利,被广泛称为一个国家“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记者更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自由成为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也作为公民一项主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相比之下,传播学就显得单调乏味,几乎与任何有特别光环的称谓无关。当然,新闻学的这种光环主要来自于新闻职业,而不是学术共同体本身。但是,高度面向新闻业的新闻学,近水楼台,就“镜中镜外一婵娟”,不分彼此了。而传播学却始终没有这样“借光”的境遇。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联姻,放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确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对于传播学最大的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借助新闻学既有的学科基础,传播学得以诞生并快速完成体制化。二是借助新闻学的价值观和使命,构建了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而对于新闻学来说,传播学的加入扩展了知识体系,增加了新闻学的科学性,夯实了学术底蕴。 但是,有得必有失。两者的结合也留下了根基上的后遗症。尤其是,直到今天,传播学也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使命,树立起可以汇聚同行,感召社会的高远理念。这可能正是传播学这一学科迄今没有“大出息”的命门所在。其实,这一个问题的困难从传播学诞生之初就一直挥之不去。Karin Wahl-Jorgensen(2004)将传播学与专业新闻学培训和修辞学的分离看作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开端。20世纪初期,大众媒体成为一种与专业教学和研究提供指导和知识地位相同的机构。20世纪末期,人们对各个领域的跨学科性有了渴望,并朝着跨学科性迈进。[27] Susan Herbst(2008)认为,大多数学科,甚至包括经济学等具有强大主导范式的学科,如今在内部都是多样化的。[28] 德国媒体与传播研究学者Peter Vorderer和Carina Weinmann(2016)认为,传播学所展现的这这种“多样性”可以被视为传播学科真正丰富的标志。但是,他们也观察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框架和方法彼此之间是脱节的。[29] Berelson(1959)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发表《传播研究的状况》(“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一文,开篇即断言,“就传播研究而言,当前状况是正在枯萎”。[30] 这种论断当然遭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们的否认和抨击。 使命与价值观与一个学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无法“无中生有”。也就是说,学科的使命和价值观总结还是时代赋予的,需要水到渠成。今天,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传播学真正进入了时代的中心位置。也进入了范式转变的关键时刻,是时候开始考虑传播学的使命与价值观。 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和生活面临重构,政治、社会和商业等面临结构性转变。数字技术在创造新的价值与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各种负面影响。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塑造数字社会的新形态,也带来数字治理的新挑战,尤其是给国际秩序带来颠覆性冲击。基于全球一体化的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时代的带来,我们急需梳理数字文明的新价值观。传播作为数字时代的枢纽。传播学,理应在塑造人类数字文明的宏大进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使命。只要在数字文明的高度上,传播学才能豁然开朗,树立其真正的学科尊严。 五、当媒介不再是信息, 传播学路径依赖的拦路石 正如施拉姆(Schramm,1971)在近五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对于研究传播,媒体和文化的学者来说,必须定期反思“传播学”的集体形象。1983年,《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特刊(special issue)对当时的传播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直至2018年,《传播期刊》在新的背景下重新对传播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新的论述。Colin Sparks(2018)认为,在媒体和传播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已经过时。批判主流思想是一项紧迫任务,有问题的概念被嵌入到大学系统中,并对高等教育中研究与教学的组织和社会角色产生影响。[31] 面对技术的革新,喻国明认为我们需要用“复杂性范式”去分析、思考和建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然而,范式转变之难,就难在系统性的超越与颠覆。而最坚固的可能是最需要打破的,原来最基础、最核心的往往也是最大的束缚。今天整个传播学科的路径依赖已经根深蒂固,锁定了无数的学者和青年学子。那么,路径依赖究竟具体是什么?路径依赖当然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整个学科固有的知识体系以及结构性的各种要素,不是简单通过局部觉醒和创新就可以获得突破,可谓“积重难返”。但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有迹可循。对于传播学来说,长期以来内容研究、效果研究和媒介研究等都先后成为学科的中心之一。所以,决定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主要是三座大山。一是长期相伴相生的新闻学;二是专业和职业长期赖以依靠的大众媒体;三是传播学从来都着眼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媒介或者媒体。数字传播时代,必须一一超越这三座大山,传播学才能豁然开朗,才能走向开阔。 1、传播学必须超越新闻学。尽管很多人说“新闻无学”,也有人说“传播无学”。其实平心而论,就学科发展来说,比起传播学,新闻学具有更加清晰而稳定的学科共同体。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或者成熟,内在的统一的价值观是最根本的体现。新闻学不但边界清晰,理论和规律也相对明晰。最突出的就是新闻学价值观非常清晰,“新闻自由”和“无冕之王”等理想和光环,尽管属于新闻职业,但是自然也与学科是一体的。相反,尽管传播学更像科学,但是,其学科始终缺乏清晰的界定,尤其确定清晰的价值观。一个学科缺乏统一的价值观,不知道“为何而学”,这是最大的问题。直到今天,新闻传播只是传播越来越小的一部分。而新闻学成熟而老道,所以让传播学走出新闻学,放弃对新闻学的相互依靠。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彻底走出新闻学,传播学就可以更加轻装上阵,更清晰地思考一下自己的根本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传播学只有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观,树立起传播学学界统一的使命和精神规范,传播学就好地站起来。 2、传播学必须走出大众媒体。传播革命如此迅捷,以至于我们这些大多数由大众媒体熏陶出来的人们,在思维模式和认知中也是大众媒体塑造出来。大众媒体曾经是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产业,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吸纳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培养的人才,成为学科就业归属的核心根据地。所以,传播学逐渐依赖大众媒体,也是顺理成章。但是,这个局面在21世纪之后就逐渐不可持续。脱离了大众媒体,传播学就将面临全新的困惑:传播学赖以生存的职业和产业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问题一时间难以有清晰的答案。但是,从技术和学科发展的趋势看,走出大众媒体,传播学失去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回到时代变革的浪潮中间,回到社会生活的主战场,回到能够让大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的新赛道上来,传播学就真正摆脱了最具诱惑力的旧有路径。超越大众传播时代,迈入新的数字传播时代,传播学才能豁然开朗。 3、传播学必须走出媒介或者媒体的禁锢。传播学研究从过去的注重内容和效果,现在又开始转向媒介,寻求突破。但是,智能传播的到来,让媒介可能也得开始“丢城失地”。包括未来的“量子传播”,可能越来越难以把握媒介的形态和意义。在互联网浪潮之前,塑造社会传播的主流媒体都是“有模有样”的,通过媒介的外在形式彰显存在。传播学基于有形的媒介或者说媒体,从来是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进入智能传播时代,社会信息传播既可以去人际化,也可以去内容化(健康码就是很好的案例),更可以去媒介化,信息传播可以直接驱动人类的行为。总之,以数字传播为基础的媒体融合与分化,使得媒介的作用已经今非昔比。“万物皆媒”的未来也意味着“万物皆不是媒”。摆脱有形的媒介或者媒体,传播学可以进一步走向解放,走向更开阔的社会和生活之中。传播学最终还得回归传播行为本身,信息与传播,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其他外在的各种延伸,都很难成为传播的本质。 趋势并没有止步,也没有止境。媒介还没有被技术“消灭”,但是,媒介越来越明显的隐形化,传播过程中媒介本身的边缘化,和媒介日渐的去意义化。媒介不再是信息,越来越成为趋势和事实。如果把未来命运越来越不可知的媒介作为研究传播的本质,很可能是舍本求末。 六、范式转变中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博弈 上述三大路径,在旧有范式中之所以突出,就是因为其本身的强大,本身对于传播学“筋骨相连”,对于传播学走到今天至关重要。而范式转变,越是重要的可能越是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关键。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放下不自己最依赖的那些知识、声誉和利益,就无法真正走出路径依赖。这是与自己长期心血的积累过不去,与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成就过不去。流连忘返,依依不舍,是最正常的心态。路径依赖从来不是简单的思想和方法问题,而是与自己以及自己的灵魂作对的问题。撬动利益和声誉的基础,比撬动灵魂还难。仅仅依靠勇气是远不够的,更需要推倒重来的底气和毅力。系统性的强大的固有学科的“向心力”,依赖是必然的,成功摆脱是偶然的。 而依然在原有路径里面寻找突破,“小打小闹”也是不行的。“几年前我们就提出, 应将 ‘媒介’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 这不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 更重要的是, 我们认为从‘媒介’入手最能抓住传播研究的根本, 显示其独有的光彩。”在传统路径中需要突围,依然找不到合适的突破点,更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具有内在时空逻辑, 能够安排和建构社会生活的行动力量而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机构和产业, 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传播研究想象力的由来。”[32] 也许,超越媒介的束缚,传播学的想象力才真正展开翅膀。智能传播时代,设备与设备之间,人与设备之间,甚至未来人与人之间,数据对行为的直接驱动,逐渐从想象变成现实,媒介的进一步“消失”已经成为新的特点。牛津大学信息哲学教授卢西亚诺 • 弗洛里迪认为,新技术发展的目的就是,就是将低效率的人类媒介从技术循环的回路中去除。[33] 那么传播学未来研究的核心路径究竟是什么?是媒介化还是社会化?是以内容为中心?以效果为中心?以媒介为中心?或者技术为中心?以传播行为为中心?还是以信息为中心?但是,这一切,都可能抓不住真正的根本。中心的调整根本上来自于实践,也就是取决于传播在人类社会或者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所决定的。今天人类全面进入网络空间为主导性空间的数字时代,传播真正从过去相对边缘的媒介而成为协调人与社会关系的枢纽。这决定了今天和未来的传播格局,必须真正回到以人为中心,才能抵达传播学的学科核心。传播成为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的生存状况是根本的,技术、信息、内容、媒介以及传播行为都可以千变万化,不断演进,多层次多方式。而围绕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稳稳确立传播学的脚跟,才能真正贯穿批判学派、经验学派和技术学派等不同学派之间的理论融合。甚至灵活和能动地贯穿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图10 传播学百花齐放的未来图景 以人为本的的传播学不但可以走出过去传统的二分法或者三分法等相对狭隘的学科体系,学科的可能性大大拓展,走向一个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正如卡斯特(2019)所说:“我不相信学科这种东西,我不相信学科之间是彼此割裂的。我喜欢传播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我们这个领域,我觉得没有边界。”[34] 基础性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都可能成为传播学新的知识来源。除了过去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技术学派等,还可以大力发展传播学的公共学派、政策学派、生态学派等。传播学提供大胆突破性创新,摆脱旧有路径,就可以真正结束长期“内卷化”的困境,而昂首走向社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关键学科。 未来走向哪里?一个学科就抓住自己本质的、不变的根本,而大胆地、开放式走向“千变万化”的浪潮中央,一个学科的活力才能最大程度展现,一个学科的价值才能最大程度释放。今天,传播学就迎来了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新明晰自己,确立自己,然后拥抱一个更大可能性和变化的新世界、新时代。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时代。这样的时代再也不是我们憧憬的,再也不是浮现的,新兴的,而是既成事实的。是传播学整个学科范式转变的“合法性”所在,也是新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使命与价值观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1、走向技术,拥抱技术。今天,技术融入生活,支撑了社会。技术再如何千变万化,依然走不出其演进的基本路径,更走不出技术根本的属性。那就是通过传播,影响和改变世界。技术并不神秘,正如洛根所言,技术是有生命力的。“技术演化与生物有机物的演化有相似之处。”[35] “科学通过常态科学繁衍组织,通过遗传、修正和选择演化,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30] 技术并不高难,我们的本职并不是钻研技术本身,而是理解技术,搞“懂技术”。而懂技术的专业和学科很多,无论是计算机学科、信息科学、电子学,甚至数学等,稍微跨一下,将知识疏通一些,都足以让传播学具备扎实的技术理解能力。新的时代背景下,不走向技术,不拥抱技术。排斥技术,畏惧技术,传播学就难以突破“低矮”的天花板,就无法走进传播的深处,无法把握传播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不被技术所迷惑,不被技术所吓阻,不被技术的变化所误导,传播学一旦拥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就真正如虎添翼。反过来,还可以为技术提供自己学科的独特的支持。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认为,技术始终是媒介。任何技术都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媒介。将对媒介的钟情移情到技术中来,传播学就能真正落地生根,形成传播学这座学科大厦的地基。 2、走向社会,拥抱社会。数字科技,联接全球,沟通世界,的确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新阶段,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新境界。变成了唯一不变的东西,传播成为社会剧变的“枢纽”。新的学科就是对“变”的回应,为新的时代新的需求提供新的知识体系,并同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科。如同传播学面临冲击一样,所有的人、机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都面临冲突。虽然变化的方向更多的是好的方面,但是,也不可避免带来负面影响,甚至走向多层次的失控。因为数字科技,每个人的时间与生活越来越走向多层次的融合,但是也面临碎片化的冲击。企业上下游更加走向整合,但是,也面临企业边界开始模糊走向离散。社会联结度不断上升,但是,社会分化也在加剧。借助技术和数据,国家治理更加一体化,但是也面临另一种撕裂的趋势。在这种历史趋势下,传播学开始置身于技术、社会和时代变革的中央,我们理应走出学科的固有领地,积极走向社会,走向变革的中央,回答重要的社会需求,为社会各方面提供知识体系,提升知识素养,提供应对之策和解决方案。 3、走向生态,拥抱生态。这个生态需要超越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也要超越“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呼应,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数字生态。虽然数字生态,依然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存在。但是,数字生态是真实的,尤其是通过数字,赋予了最真切的存在感。有了数字的基础,数字生态就有了实在的抓手。从数字传播学到数字生态学,将是未来传播学的一大新的突破和提升。数字生态学,将走出传统学科的狭隘,走出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偏颇,而走向更加对新的时代与世界更完整的认识。数字生态需要超越技术,超越内容,超越媒介,甚至超越“地球村”。人类社会的生活基础从此既基于现实世界,又基于数字的虚拟世界,双重空间的互补、联动与融合,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传播学,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自己新的知识体系,形成自己新的学科使命,赋予学术共同体每一位内化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当然,有人担心,去新闻,去内容,去中介,那传播学还有什么?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是,也不需要多担心。新闻、内容和媒介等依然是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只是不再是中心位置,也不再是重点。那么,跨度太大,会不会让传播学偏离自己的主业,而更加散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当下并不需要多操心。因为,当下首要的任务还是如何摆脱路径依赖,从原有的轨道上挣脱出来。也就是说,首要的还是如何走出来的问题,这属于处于被动局面的“痛苦的烦恼”。而对于挣脱出来之后的下一步,则属于处于主动局面的“幸福的烦恼”。两者不可相比,起码有个先后。 更何况,即便困难再大,进程再慢,我们也不必悲观,可以保持乐观。因为无论如何,今天传播学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已经非常庞大,汇聚精英好汉无数,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更是值得期待。无论路径依赖多么强大,堡垒依然会从内部先攻破。只是时间而已。学术共同体由千千万万富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们构成,其生命力和能动性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生生不息的学术共同体不可能受控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学说,其内在的创新和变革力量始终剧烈地活跃着,形同巨大的活火山,时刻可能喷涌而出。这一切,一定会发生,虽然我们很难准确预测究竟是谁脱颖而出,究竟什么时候水到渠成。一切都是未知的,却是板上钉钉的。蓄势待发的阶段,也正是历史最精彩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其中,也参与其中。 数字技术已改变整个世界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面临新的命运抉择。传播学第一次置身于时代大变革的中心。而真正站在人类生存状况的全局上思考的学者中,卡斯特是为数不多的一位。作为为数不多摆脱了传播学路径依赖的学者,走出了学术新的开阔大道。卡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通过卡斯特看传播学的未来。传播学需要站在人类生存状况的高度上,需要在推动和塑造人类新的数字文明的层次上,找到新的定位!卡斯特在他的学术自述中如此写道:“在我学术历程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对构成社会基石的权力关系的研究。在我研究都市化时,都市问题对于新的政府政策和新的社会运动如何形成至关重要。如今,传播领域——包括新技术环境中的新媒体和传播的横向网路——是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传播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运作的中心,因此,在过去10年,我决定进入这个领域。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一以贯之的思路。”[36] 图11 施拉姆期望的未来传播学: 行为科学统一体的基础 当然,摆脱路径依赖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往往在失去旧有理论的依靠之后,面临着新的进退两难。正如卡斯特对自己的处境的描述:“但是,一旦我将技术范式和数字通信作为社会变革的杠杆进行了分析,从而重新定义了权力关系,我就会发现自己很孤单。有些技术人员和技术先知对兜售未来学更感兴趣,而不是将人类状况的根本转变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一些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常常将整个与新技术相关的问题视为技术决定论,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网络分析、数字文化或网络社会运动等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对我们已经进入的新的工具世界非常敏感并且很有文化素养;但是他们几乎不能依靠适当的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将深层理论的传统与他们的新颖而有趣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力量社会理论了。”[36] 卡斯特的尴尬是今天传播学突围的写照。但是,除了前行我们别无选择。今天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路径难以为继,更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我们前方已经打开了一个更开阔、更精彩、更富有使命感的新世界。在数字传播的新格局下,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能真正搭建出传播学的理论大厦,真正实现施拉姆20世纪80年代设想的传播学成为“人类行为科学统一体”基石的学科理想,确立传播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总之,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空间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传播学有了自己全新的使命。那就是探寻和推动人类数字文明,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让世界更美好。向着技术演进的方向,向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向着新文明的方向,就不会迷失。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想象,去探索,去实践。确立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和使命,重树传播学的学科尊严就为之不远。 参考文献 [1] 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第132-147页.[Fang Xingdong, Yan Feng, Zhong Xiangming,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Shifts from Cathedral to Bazaar”, Modern Communication,No.7(2020),pp. 132-147.] [2] Mills. C.W,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3] Internet World Stats, 2020,April 15,2021,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4] 参见:达里奥:冠状病毒疫情标志着“新未来”的开始。https://finance.sina.cn/forex/whzx/2020-04-22/detail-iircuyvh9230188.d.html?vt=4&wm=3049_0005354658641 [5] 方兴东,钟祥铭,严峰:《论数字传播学的崛起——传播学新范式的演进历程、知识体系和路径选择》,《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1期,第37-51页.[Fang Xingdong,Zhong Xiangming,Yan Feng,“On the Ris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 Evolution, Knowledge System and Path Selection of New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News & Writing,No. 11(2020),pp. 37-51.] [6] 高名潞,陈小文:《当代数码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Gao Minglu,Chen Xiaowen,Contemporary Digital Art,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5.] [7] 单波,侯雨:《思想的阴影:西方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5-35页.[Shan Bo, Hou Yu, “The Shadow of Thoughts: Critical Review of the Ancient Greek Origin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No. 12(2017),pp. 15-35.] [8] Rogers. E. M,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4. [9] Williams. K.R,“Reflections on a Human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3(1973),pp. 239–250. [10] 方建移:《传播学研究的科学取向与“人”学迷失》,《未来传播》,2019年第6期,第42-47页.[Fang Jianyi,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Lost of " Human”, Future Communication, No. 6(2019), pp. 42-47.] [11] Lang. A, “Dynamic Human-Center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or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o.1(2014), pp. 60-70. [12] Polletta. F, “Social Movements in An Age of Participation”,Mobilization, No.4(2016), pp. 485–497. [13] Obregón & Tufte, “Communic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5(2017), pp. 635–645. [14] Craig. R. T, “For a Practical Disciplin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2(2018), pp. 289–297. [15] 喻国明,方可人:《传播媒介:理论认识的升级与迭代——一种以用户价值为逻辑起点的学术范式》,《新闻界》,2020年第3期,第34-41页.[Yu Guoming & Fang Keren, “The Update of the Concept of Media: A Paradigm Based on the Value Perception of User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thly, No.3(2020), pp. 34-41.] [16] 苏敏,喻国明:《以人为本的成长逻辑: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25年——基于学术视角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27-141页.[Su Min & Yu Guoming, “People-Oriented Growth Logic and the First 25 Year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of Citespace”,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2019), pp. 127-141.] [17] 方兴东,钟祥铭:《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现代出版》,2021年第2期,第37-45页.[Fang Xingdong & Zhong Xiangming,“The Ess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et platform antitrust”,Modern Publishing,No. 2(2021),pp. 37-45.] [18] Baron. N. S, “Who Wants to Be a Disciplin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o. 4(2005), pp. 269–271. [19] Donsbach. W, “The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3(2006), pp. 437–448. [20] Sukhova. M (2016).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December 12,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auriga.com/blog/2016/digital-transformation-history-present-and-future-trends/. [21] Gantz. J & D. Reinsel, “The Digital Universe in 2020: Big Data, Bigger Digital Shadows, and Biggest Growth in the Far East-Western Europe”, IDC, February 2013. [22] Hilbert. M & Lopez. P,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Store, Communicate, and Compute Information”, Science, No. 6025(2011), pp. 60–65. [23]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 [24] Andrews. et al., “What Will 5G Be?”,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No. 6(2014), pp. 1065–1082. [25] Carey. J. W, “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 E. Dennis & E. A. Wartella(ed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21-38. [26] 蔡宗模,毛亚庆:《范式理论与高等教育理论范式》,《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第6期,第52-58页.[Cai Zongmo, Mao Yaqing, “The Theory of Paradigm and the Paradig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Fudan Education Forum, No.6(2014), pp. 52-58.] [27] Wahl-Jorgensen. K, “How Not to Found a Field: New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3(2004), pp. 547–564. [28] Herbst. S, “Disciplines, Interse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4(2008), pp. 603–614. [29] Vorderer. P & Weinmann. C, “Getting the Discipline in Communication with Itself”,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2(2016), pp. 211–214. [30] Berelson. B,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No.1(1959), pp. 1-6. [31] Sparks. C, “Chang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Wor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2(2018), pp. 390–398. [32] 胡翼青:卷首语,《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4期,第1页.[Hu Yiqing, Prefac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No.4(2020),pp. 1.] [33] 西亚诺 • 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Luciano Floridi, The 4th Revolution, Trans by Wang Weng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pp. 27.] [34]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与传播力》,《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74-92页.[Castells. M,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Power of Communication, Trans by Cao Shule, Wu Jingwei, Dai Jia, Lu Jia, Jin Jianbin,Global Media Journal, No.2(2019), pp. 74-92.] [35] 罗伯特·洛根:《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Robert Logan, What is Information? Propagating Organization in the Biosphere, Symbolosphere, Technosphere and Econosphere,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 China Encyclopedia press, 2019.] [36] Castells. M, “A Sociology of Power: My Intellectual Journe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42(2016), pp. 1-19. [责任编辑:孙梦如]